来源:网友投稿 2025-05-02 06:57:00 热度:196°C
原标题:T.A.B|智能跃进:艺术生产系统如何演化?缪晓春·陈抱阳·董亚楠·高一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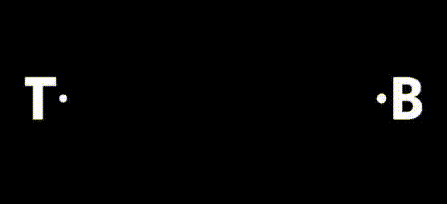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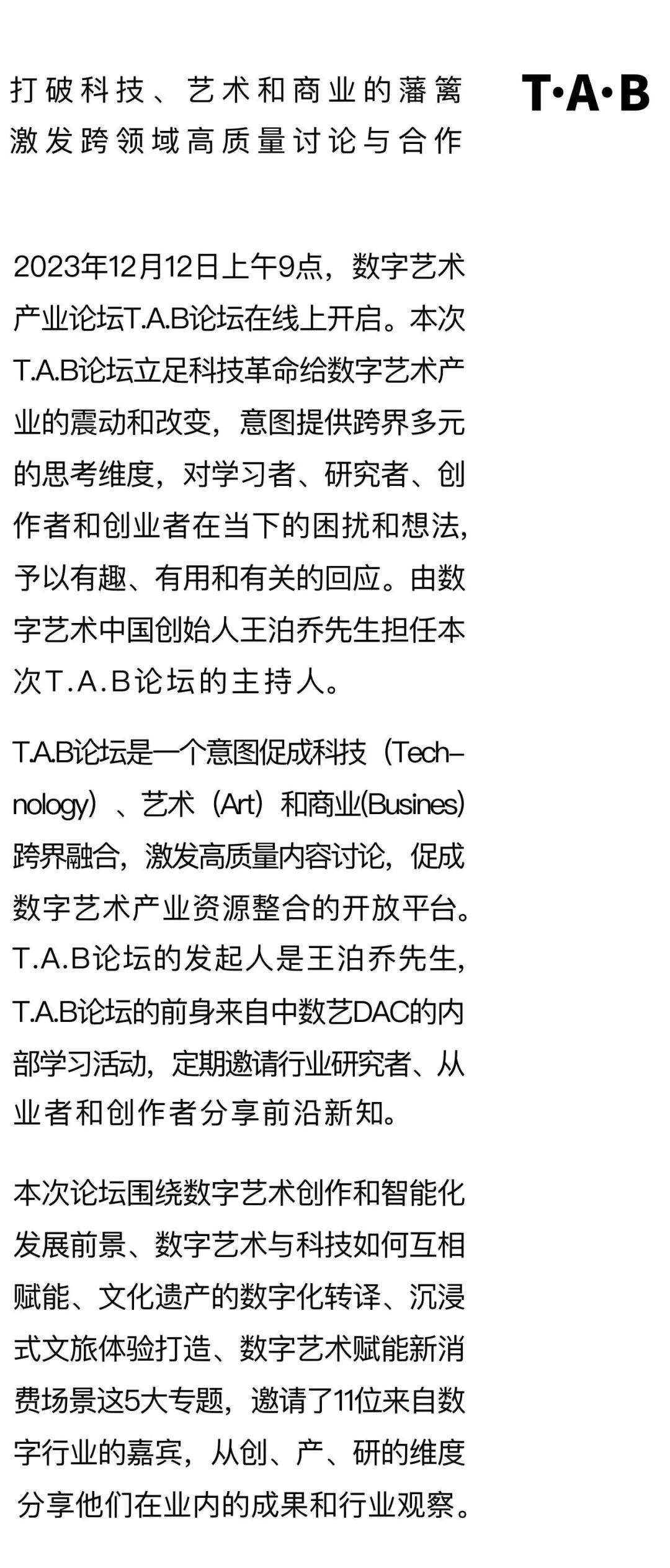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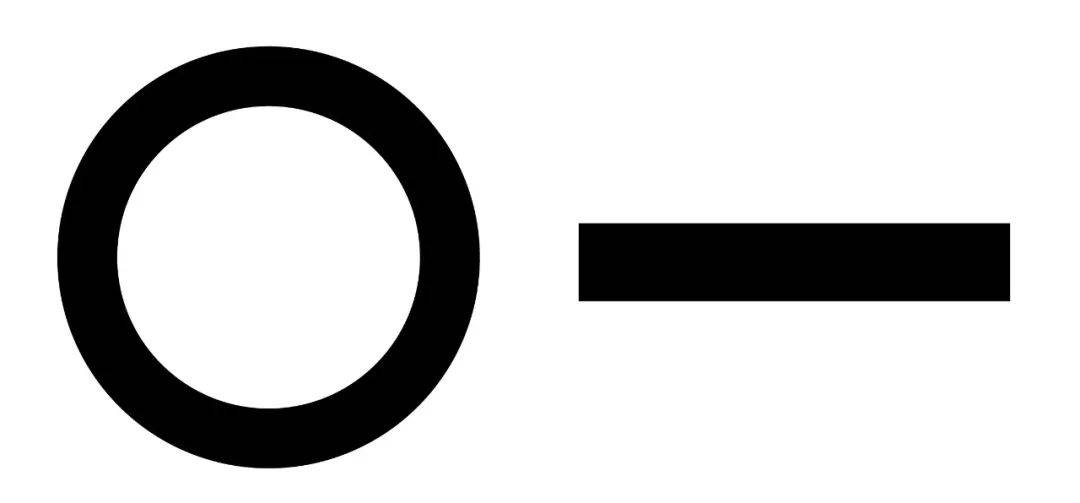
前人工智能时代的
数字艺术创作

嘉宾:缪晓春
艺术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观察一
数字技术和艺术发展时间很短
需要不断的尝试和积累
数字艺术的发展时间很短,也就那么几十年,好处就是没有太多的大师竖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以非常大胆地去做,但同时很多事情需要自己不断的去试错,以取得某种经验。每个时代都会产生各自具有强烈时代特色的作品,技术手段是其原因之一。
观察二
在数字工具的能力边缘进行
文艺考古和艺术实验
在作品《虚拟最后的审判》(2005年)里,我用一个三维数字人物模型取代了米开朗基罗原画当中的400多个人物,并建立了一个可以“漫步”其中的虚拟空间。原来只能从前面观看一幅画,现在增加为前后上下等五个视图,把二维的平面画面转换为三维的立体空间,同时又做了一个三维电脑动画,把静态图像转变成了动态影像。于是出现了某些意想不到的效果。

▲ 缪晓春《虚拟最后审判—正视图》
调节软件的各种参数,看看随之而带来的效果是否有用。有时强烈的数字变形会让人想到表现主义的情绪表达,鲜艳的色彩通道又与野兽派有所关联,我戏称之为“电脑野兽派”,而基于时间的数字雕塑承继的是未来主义对时间和速度的激情。

▲ 缪晓春《坐井观天》,三联画

王泊乔:
您不管是对西方美术史的研究也好或者说是重构也好,对东方绘画的探索也好,完全是带着一种冷静的思考,是用当代的这种数字工具手段进行的。其实目前人工智能出现,其实你就看到这个技术进步是巨大且不可阻挡的,您之前在AI展览里也提到了算法艺术形式主义的焦虑,怎么看待技术变化和人的创造力的问题呢?
缪晓春:
是,我们是可以在艺术史里面来回穿行的,从古到今,从今返古,从东到西,从西到东。在不停的交流和碰撞中产生全新的想法。
这也不是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只有前行没有回归,同时也会遇到很多问题。我们现在可能技术越来越成熟,但并不意味着运用这些技术手段的作品会自动的变得更好。
我有这种感觉,我现在做的作品好像是属于前人工智能时代的东西,Art pre Ai,就是说,它已经有电脑的辅助和软件的贡献,但远未完善,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艺术。想想那个时代到来之后,我能做什么?也许我什么都不需要做了。所以我假设我自己的东西是前人工智能时代的艺术,就像拉斐尔前派这个名词想表达的那种意思:在拉斐尔之前,艺术非常质朴,虽然没有拉菲尔那样高超的技术,但并不妨碍它里面已经有了真挚的情感。
王泊乔:
因为数字工具的这种便利性、普及性,人人都是艺术家这个时代好像已经来了。但是因为这种普及,作为一个艺术家的门槛儿好像又更高了?我是看到您,不管是从05年开始做的数字作品,好像隐隐约约有一个美学体系的,它不是凭空来的,而不是就是随便堆一堆,拿一些素材做一做。
缪晓春:
对,我们正好处于这种过渡阶段,我觉得这个过渡阶段也挺有意思的:它既可以承接古代艺术的美感,这是我无比热爱的,也可以去借由新的技术手段生发出全新的视觉经验,这是我无比向望的。
▲缪晓春《陀螺舞》, 动画片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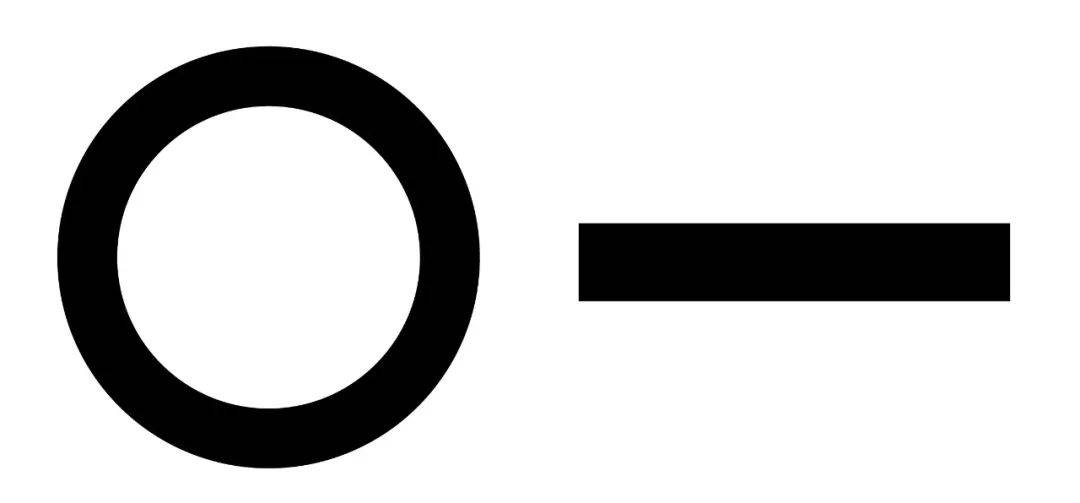
不可能的即兴:
AI x 艺术生产

嘉宾:陈抱阳
青年艺术家、策展人、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与科技艺术学院教师
观察一
人工智能时代的艺术创作:从追求生成结果转向设计模型
人工智能时代的艺术创作:从追求生成结果转向设计模型从去年年底到今年,AI的发展状态与之前这几年的一个区别就是算法来到了一个很成熟的阶段,算法对于生成结果的可控性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所以在今后的创作中,相比对算法的调优和对好的生成结果的追求,会转变到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更好地推动艺术生产。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创作者应该花更多的精力研究怎么给出一系列规则,训练出一个自己的人工智能模型。当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到今天,又链接到了当代艺术、观念艺术的叙事。

▲ 陈抱阳《假蜃楼·迭代1·意识欺骗》,2023
人工智能仿真模拟(屏幕、大语言模型、实时演算)

▲ 陈抱阳《假蜃楼·迭代2.1·共生移民》, 2023
大语言模型驱动的智能体
(导航算法, 屏幕,投影, 实时演算火星仿真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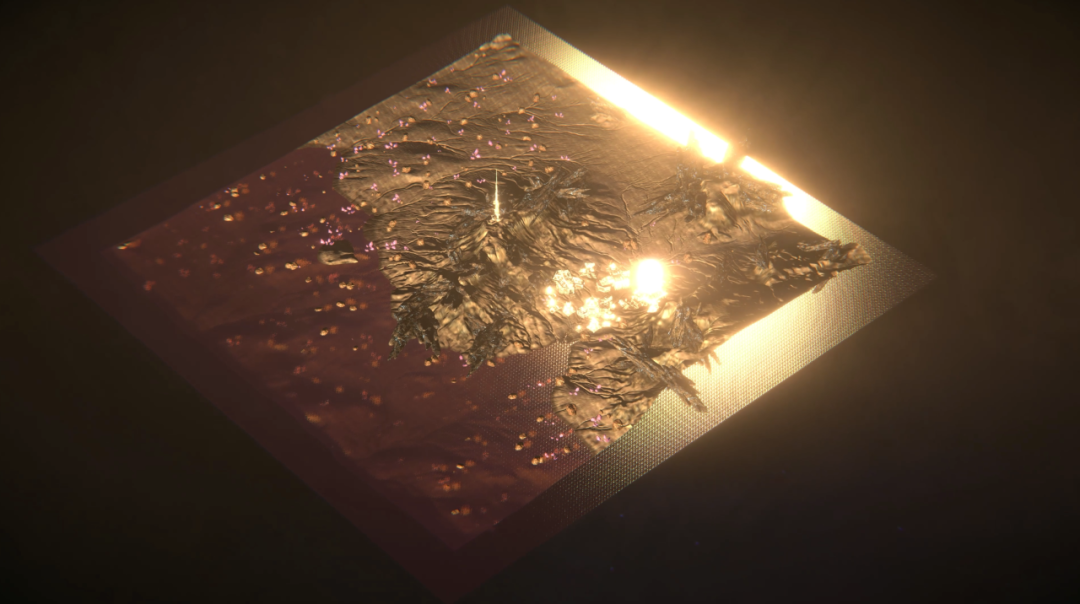
▲ 陈抱阳《假蜃楼·迭代2.1·共生移民》, 2023
大语言模型驱动的智能体
(导航算法, 屏幕,投影, 实时演算火星仿真空间)
观察二
在数字工具的能力边缘进行
文艺考古和艺术实验
工程化是指在某种产品、项目或系统的设计、开发和运作过程中将一系列最佳实践、标准化和自动化应用于其中,以确保其高效稳定、可靠和可维护。在一个皮影的创作项目中,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学习了传统皮影的创作手法和效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完成了算法实现了艺术创作的结果,还搭建了一个创作平台,这个平台让每个人都可以来创作一段皮影的动画,希望可以借年轻人对AI的好奇激发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好奇。
▲图 AI+art白皮书,任务工程化
观察三
人工智能会不会取代艺术家?
如果把人工智能里面的工智能三个字去掉,问题就变成了“人会不会取代艺术家?”其实很多时候人是一种矛盾的状态,有时候我们会说,人工智能是人创造出来的东西应该是听命于我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又会浪漫地想象,这个技术以后就会成为一个艺术家。
▲ 陈抱阳《重构山水》,2014,人工智能生成
如果把人工智能里面的工智能三个字去掉,问题就变成了“人会不会取代艺术家?”其实很多时候人是一种矛盾的状态,有时候我们会说,人工智能是人创造出来的东西应该是听命于我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又会浪漫地想象,这个技术以后就会成为一个艺术家。
▲ 陈抱阳《仿生人会梦见电子奶牛吗?》VR影像片段
这个关系启发了我创作了一件作品,用两辆由AI驾驶的小车进行简单的追逐游戏体验。观众可以通过放置障碍物来影响小车的追逐过程,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就想去说,这些技术可以被我们人很简单的改变。
▲ 陈抱阳,AI小车系列《追逐迷雾》影像片段
王泊乔:
科技的发展对艺术意味着什么?因为现在很多的作品是只剩科技没有意识、思考,它只是有那么一个形态,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
陈抱阳:
在五年之前,我也会不停的反思,就叫做算法形式主义。我的作品就是因为用了这种新技术,这是它成立的唯一的这么一个支撑点。从客观上来讲,一个技术在发展的过程中,它都会有这么一个阶段。在去年之前,大家都是在对于算法的研究怎么样能够让一个算法能够把书法给生成出来。下一步才是生成出来的书法要好看,好看的标准是什么?我认为的好看,你认为的好看,他认为的好看,那么其实这种标准的建立,它就是很艺术的一些部分。比如说我们学习书法,其实在学的时候就是带有评价标准,当我临摹了几遍以后,可能就总结出一些自己的绘画思路。
对于一个好的创作者来讲,做完技术尝试以后需要总结人工智能对于我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帮助和变化?AIGC从生成结果上来讲,它跟画画相比在生产机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如果我的目的是获得一个模型,我的模型被别人拿走以后,它可以继续去生成我标准下的内容,这可能就对生产的机制产生了改变。现在艺术家可能就是一个平台,你创造了一个平台,大家来共同来生成那么一个作品。
王泊乔:
我也看到您的很多的实验性的作品是不是也有一种商业的可能性?我所谓的商业性就是它变成某一个展览,或者说更多的第三方进来参与这个项目,通过文旅还是这种商业合作,让它传播的更广。
陈抱阳: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处于这个被包围着的数字的时代了。首先,市场有这个需求,它需要这些数字的内容来满足大家的这个文化的这样的需求。第二,我觉得艺术本身的发展,也越来越强调它要能够跟社会产生链接,要能够服务社会,通过一个作品能让我们社会的美育有提升,或者说提升大家的一些对数字技术的认知和素养。
▲ 陈抱阳《第一森林定律》,2021
人工智能装置(机械臂、烟雾、灯光、树)
▲ 陈抱阳《从河工到银河》, 2022
人工智能装置(机械臂、投影、烟雾、灯光、毛竹与船桨)
迷路:
数字艺术 IP 原创
不止于书
嘉宾:董亚楠
青年数字艺术家、中国恐龙 IP 创作者
思考一
创作者与新事物的融合会成为态,
但创作的关键在于艺术家的自我表达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创作者,只要没有绝对的一个封闭状态,或多或少都会使用一些数字手段介入创作。数字艺术现在还算是一个比较新鲜的名词,可能是因为今天的艺术创作者对技术的使用还处在比较前期的阶段,没有到深度融合、普及、习以为常的程度。不论创作是用什么方式、媒介开始的,任何一个艺术家做的事情终归是在整理和表达,在传达他对于这个时代、生活或对于某种变动的感受。
▲董亚楠《时间永远分叉通向无数个未来》ZINE,2023
现在正处于一个AIGC技术爆发的阶段,不断地出现新的概念、智能工具,迭代速度很快,也具有相当的冲击,技术爆发会发展入到下一个阶段。现在技术迭代很快,对AI工具的使用还处在一个比较有新鲜感的阶段,这种情况以后也会成为一种常态,其实你会一直处在这样一个与新的事物融合,然后创作、发展的一个状态里,这种持续的变化是不变的。我们应该在这种快速迭代的日常里找到那个不变的东西,找到一种平衡。
▲董亚楠,迷路 数字艺术书展,概念设计
思考二
创作者要不断地接触新东西来让
自己的表达方式更多元
有时候创作者是需要接触新东西来让自己的表达方式更多元,AI工具是很有效一种补充,尤其是当你到了某一个阶段,做不下去或需要做出改变、提高效率的时候,新工具会帮你打开一个新的思路,了解、接触新的创作工具也是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
思考三
创作者的思维训练:
对恐龙宇宙IP的想象、创造
和衍生开发
《恐龙快递》算是我的恐龙题材创作的开端,从这本书开始,我开始练习把虚拟的东西在脑子里完整地进行构建,并把它表达出来。做图画书的过程中,没有觉得我是在画一张一张的画,更像是在打游戏一样,持续在开阔、搭建一个世界。
▲ 董亚楠,恐龙艺术家系列
曾经想象在恐龙的时代,如果有某些著名的艺术家存在,他们会是什么形态,如果是恐龙的样子应该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就有了恐龙艺术家这个IP。把艺术家画成了恐龙版,保留了他们本身的一些特征。对应的还画了一些恐龙蛋,结合了艺术家的成名作。有时候是作品成就艺术家,人和物的关系有时候是双向的,这个系列叫《蛋生》。后来还画了其他的艺术家,如大卫·霍克尼,这个系列后来也做过一些互动场景、游戏设计。
▲ 董亚楠,恐龙艺术家系列
▲ 董亚楠“恐龙艺术家系列”《大卫·霍克尼》
《中国恐龙地图》是我第一次跟古生物工作者合作做的科普类地图书,是我的恐龙宇宙的探索、整合阶段。从小就对恐龙比较感兴趣,其实不只是恐龙,对古生物都很感兴趣,包括对长时间线之前的古植物同样感兴趣,也许我感兴趣的是时间本身,当时间的跨度到了一定量级的时候,一切和你所在的现实就会有一个巨大的反差,这时需要大脑去发挥想象力填补一些空白,这个过程是很有意思的。
▲ 董亚楠《中国恐龙地图》,恐龙全图
设计的时候想在常规科普书的基础上做一些不常规的事情,尽可能在图文之外,书籍结构、材质上也花一些心思做一些变化。
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大家印象里恐龙是某一种动物,但其实恐龙是一个很庞大的生物群体,它可能比我们现在所说的哺乳动物这个群体还要更庞大。所以当我在画完300多种恐龙的时候,会很自然的接受它们这种个体差异以及外貌差异如此之大的这个事实。通过这本书,有机会对恐龙进行系统的梳理,这种梳理让我更深入的去认知和表达这个题材。
▲ 董亚楠,恐龙系列
王泊乔:
恐龙宇宙是一个巨大的虚构世界,那你怎么看如何营造虚构世界的沉浸感?
董亚楠:
真正的沉浸式设计一定是让内容与人产生关系,如果内容与我没有关系,就不是完全沉浸式的设计。比如我们创建了一个虚拟的侏罗纪花园,里面有正在孵化的恐龙蛋,观众必须以自己的视角与场景互动,主导情节的走向,才能完全沉浸其中,而不仅是作为一个旁观者。
另外,若设定一个完整的故事让观者跟随,观者不感兴趣,就可以不听这个故事,也就没办法进行沉浸式体验,所以内容要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设计,增加参与度,减少排他性。比如让观者在不同的故事节点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走向不同的结局,内容相对开放、不设限。所以我们可能设计的是一个框架,就是让大家更容易沉浸进去,让大家能够在基础设定之中,叠加自己的想象力和感受力,变成一个与“我”有关的沉浸式体验,不只是艺术家在表达自我,或只是做一个视觉效果。而是让所有人的这种情绪和感受共情,能量能凝聚在一起。沉浸式数字艺术需要有人的介入,才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王泊乔:
在进行设计调研的状态和流程是怎样的?
董亚楠:
我的方式是偏向发散而非线性,虽然之前考虑过线性思维是否更有效率,但我很难完全按直线工作,对我而说,调研和实践是反复进行的。先进行初步调研和基础了解,期间会出现一些零散的想法,就像星星在空间中散落,暂时还没连接,会先记录下来。进一步深入调研时,这些想法之间可能会产生联系,有些也成为新的原点,发散出一些线。然后再按照形成的思路进行,但如果在实践中发现了解还不够,就会返回重新调研。
▲ 董亚楠《兔恐龙》,Rabbitsaurus 白垩纪的占卜者
设计考古下的
意义创造
嘉宾:高一强
“日用之道”创始人及品牌合伙人
中国室内装饰协会设计专业委员
中国家具协会设计委员会会员
中国陈设委员会副主任
北京设计学会会员
思考一
设计的知识考古:
缩短产品到用户的距离
我们的产品或作品如何能跟观众瞬间产生共鸣?很多时候所谓的设计,最后是一个价值和意义的再构建的过程。大家试图用各种技术解决问题,技术变化日新月异,但是人的生物性结构是没变的。回到对人的生物性结构的研究,也就是在社会学的条件下和行为学的条件下来研究人的认知心理,当我们把这块儿打通,其实再做创作或设计,你会发现技术对我们是如虎添翼。
▲ 图 高一强提供
所以我们日用之道现在的逻辑就是,人对事物的认知是他记忆和经验的一个再识别过程,它涉及到人记忆的认同的具体性和重构性,当信息通过感知进入大脑的时候,其实是人的生理性反应和知识结构在同时作用,然后再选择是不是接受这个信息,这就牵扯到新信息里是不是有他的记忆和经验能够来比对,如果有他就马上会接受。
当你研究了人的认知,你能迅速在产品跟人建立一个瞬间沟通的渠道。设计师迪特拉姆斯说我做的就是把A到B的距离缩到最短,A就是产品,B是用户。很多设计者都说我试图缩短两者的距离,但我们真的了解用户吗?换句话说,设计师在做作品的时候真的了解用户吗?很多时候不是的。
去年在巴黎应用技术博物馆,当我看到最老的福特车时,我才意识到福特的悬架结构还是马车。所以如果设计者不研究原来事物的形成过程和模型,你的设计就没有根据,如果你出来一个特奇怪的东西,使用者就不认。好多人都喜欢戴森,为什么呢?你会发现戴森完全复原了我们小时候对风的感觉,三叶电扇吹来的风你会觉得这风是假的,戴森把三个叶片摘掉了,看不着叶片动,就觉得有风过来,所以你会觉得它很美,这就是设计师捕捉到了一个物或者事的根本价值和意义。
▲ 图 高一强提供
思考二
应用认知规律可以优化
公共艺术空间设计
在做深圳前海交通枢纽整个的艺术和设计顾问时,我们大量的应用了认知逻辑,比如说按人的视觉而言,140米的范围是最能确定安全性的,从人的生物性来讲,在这个距离人看到的正好是事物的颜色和大概形态,我们在跟景观公司做对接的时候,你就发现我有依据了,不需要跟甲方争论什么是美。我们利用这个方法帮甲方做了一个漏斗,用来测量是不是要在140米左右要出现一些景观或者休息区。比如人的疲劳距离其实是1500米,最舒适的距离是778米,那在做景观包括做一些艺术作品的时候,这些地方都需要设计方考虑清楚。
王泊乔:
虚拟世界当中也有这种虚拟人、虚拟宠物,甚至还有虚拟饭菜,对很多虚拟场景的建构,能不能应用到您的这个理论,或者说您这个理论对这个世界的构建会有什么帮助?
高一强:
其实是一样的,虚拟世界的再现是以现实社会的社会结构为基础的,现实社会作为原型,里面是有离婚交通拥堵,这些主观的不美好的东西,虚拟世界是以它为参照做一个美好的东西。
所以虚拟世界其实还是对记忆和经验的再挖掘,我们认为可能虚拟世界当中就不需要把这个桌子做的那么的精美了,拿素材堆一堆,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元宇宙展览或者VR的那种,大家不愿意在那里边常待呢?因为它没有美学,对人来说没有熟悉感、记忆、联想,它非常陌生、没有跟人产生某种有关系,所以他就冷冰冰的,根本就让人待不住。但是我在想未来会出现一种可能超越真实的某种东西,因为你在虚拟世界里边,你可以获得比真实更真实的触感,比真实更真实的视觉,比真实更真实的味觉。
现在我们所说的虚拟世界,它把我们的五感丢了好几个。我们现在其实只用听觉和视觉,触觉都很少,嗅觉基本就被放弃了,这个时候其实就考验我们对人的认知理论的研究深度了。比如说怎么做数字展览的视听?哪个声音是前置,哪个做干扰,再比如虚拟世界里的画面怎么做加帧怎么做减帧?
我来的路上读了一篇文章,是说完美主义导致抑郁症。就像我们在做的虚拟世界,我们原来都是被爸妈教育成是一个100分的好学生,但其实我们就没有想我们反向思维的时候,在虚拟世界一定有对比,它才能觉得快乐。现在我觉得我见过一些展览,他们做的就是太趋于100分的状态了。
王泊乔:
感谢高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分享,让我也有好多启发。我们现在一味的做艺术科技,真要往回去想一想,如果现在的这个组织者策展有这种多媒体的手段、又掌握认知心理学的方法论,也许这种展览真是能够给更多的观众,不管他们是什么知识背景、经验层次,甚至是不同种族的人,他到了这种展览现场。通过多种感知体验或记忆的连接联想,或许能获得某种所谓的咱们现在流行说那心流的感觉,就是能给人带来启发感动、欣喜愉悦的心情,我觉得这是艺术莫大的功能了。
高一强:
我们的实验性或者技术性之所以变得很偏执,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打开。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展览都在做宽度,深度没有。比如说我们对声音逻辑的调整,我们如何把视觉转化成触感?
我去年看了美国一个医学院的论文谈视觉触感,比如说画面里有一种尖锐的东西,你看到就会有一个头皮发麻的感觉,欧洲和美国他们整个的学术研究回到了人的基础结构。之前有一个特火的视频,是一个针扎假手的实验,其实受试者明明知道真手在旁边,被扎的是假手,但他的视觉已经把他欺骗了,当针扎在这个假手的上的时候,他也会疼,视觉触感就来了,这是一个知觉重构的例子,我觉得知觉重构是未来博物馆的一种方向。幸福和快乐是大脑给自己的一个奖励机制,那我们如果能激活这个奖励机制,大脑就会有幸福的感觉。咱俩的路径正好是反着的,你刚才描述的是我怎么样把这个幸福做起来,我们研究的路径是大脑如何给自己一个奖励机制。
▲ 图文 高一强提供
编辑/章媛
中国传媒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
数字艺术研究者
责任编辑:
新疆首个储能集控服务一体化平台实现数据可视化高马尾逐渐消失在校园,“鲶鱼头”更受欢迎,家长不理解也看不懂
VITA地平线华语青年影展闭幕,演员赖冠霖分享跨界导演心得新京报2024-01-07 11:56新京报2024-01-07 11:56